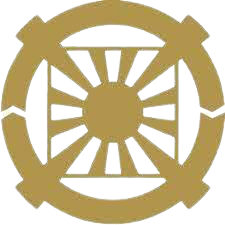我相信無論是在追求無形之永恆真理或有形之現象的觀察,在不同的學術領域中所探究的內容都有著一定的關聯。事實上,一件事情如何能在某個時空中發生,除非有某種看不見的因素存在。
宗教與哲學所關心的形而上及道德的問題,是長久以來盤據著人類心靈意識的問題。人從何處來?為何人生總有許多苦難?何謂善與惡? 死後是否有來世?無論我們各自所持有的學識理念為何,這些問題都與我們密切相關。
以我之見,所有的知識領域——從神學到自然科學,除非具有能夠讓人理解的目的與方向,否則皆不具有任何意義,追求知識價值之標準即在於探求這個目的。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人們將發現所有不同學術領域所探求的內容總是彼此相關。理所當然的,真知是不可能互為抵觸的。事實上,在某一領域中的發現可能會給另一領域的研究帶來重大的衝擊。在本世紀,科學的發現帶給一直在追求所有知識之個人的行為及信念很大的衝擊。舉例來說,相對論與測不準原理之間儘管有許多的分歧,但無疑地,它們對哲學與神學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令人不忍見到的是,雖然在各個領域中的研究都是互相關聯的,但學者們常常會傾向於只專注於自己的研究。專門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知識,但除了研究者自身以外,它所帶給全體的意義可能只有一小部份。發現的喜悅應該能夠激勵學者以著大眾都能夠了解的觀點向外界發表,身為學者的我們更應當樂意聆聽,以免我們的見識變得膚淺而狹隘。
過去宗教界人士曾對科學的發達感到備受威脅,特別是自文藝復興時代開始。但是,宣稱不斷地關切人類救贖的宗教人,怎能忽視這些解決人類飢饉、疾病、衰老、住宅與衣服缺乏等問題的知識與科技之發展呢?科學的貢獻確實為人類解決了許多的問題。 ﹙第六屆ICUS(註1) 1997.11.25-27美國加州舊金山﹚
儘管科學發達與經濟繁榮,世界上仍有許多的痛苦不幸;儘管科學家們懷有深遠的願望與勤奮的努力,貧窮、文盲與疾病仍舊在先進國家中盛行;不安、戰爭與敵意仍舊存在於國與國之間。因此,即使是處於富裕的已開發國家的人們,仍然持續地在遭受苦難、悲傷和痛苦。
許多的領袖們正嘗試著要消弭這些苦難,並建立真正的和平與安定,但這世界充斥著卻是和平的空口號,人們正陷入在深深地不安、焦慮及恐慌當中。這是從何而來的呢?主因乃在於規範人心的價值觀已逐漸地敗壞,隨著倫理道德力量的喪失,善的準則也已消逝。
沒有人能夠否認,任何被造物包括人類都是由兩種本質所構成的統一體——外在物質本質與內在心靈本質。人是心與體的統一體,動物是體與本能的統一體,植物是物質與指向性生命的統一體,而無機物是物質與指向性能量的統一體。
為了實踐愛,必須樹立準則,因為真愛的生活需具備秩序。在一個秩序已遭到破壞的社會裡,真愛的生活是無法在和諧中施行的。也就是說,真愛的生活需要有秩序,而秩序需要準則。準則意味著能規範人類行為的律法與原理,即倫理與道德。因此,為了擁有以愛為中心的善生活,人們需樹立健全的倫理道德思想,並且需親身實踐它。為了這世界所提出的倫理與道德規範,必須是清楚且適合於現今社會的人性。過去的倫理道德規範為何會逐漸地衰敗,部分原因乃在於現代人傾向於唯物主義論,而部分原因乃在於過去的價值觀已無法滿足現代人理性上的需求了。由此看來,建立新的倫理與道德觀成為絕對必要之事。那麼新的價值標準要如何建立呢?唯有建立源自崇高、圓融、完整的思想體系,才能統一所有過去的哲學思想與宗教教理。
所有過去的哲學思想與宗教信仰當中,都擁有對人類帶來益處的有力觀點,卻因為這些思想未能被調整以適用於這個新世紀,乃至於今天已漸漸地被人們所遺忘。由此可知,為要建立一新的價值體系,我們必須吸收所有在舊有價值觀中的有力觀點,以此發展出適用於現今人們所需的新價值觀。
這些意見分歧的專門化科學,就像是解體的機器,最終會導致整體中的單一功能癱瘓,而使得科學無法完成它的使命。
人類也是由一致性原因所構成的統一體,總地來說,人類不能被視為僅是物質的存在或僅是心靈的存在。因此,只有物質生活的改善是無法獲得幸福的,唯有當物質與心靈的生活同時提昇的時候,真正的幸福才會來臨。
科學因其本身的範疇被限制在物質面,而使得一直以來科學總是致力於物質面的提昇。因此,雖然科學家們都懷有熱切的渴望並辛勤地工作,人類仍未能逃脫苦難與混亂。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締造心靈改革的運動呢?為此,我們必須樹立起善的標準。而為了決定善的標準,必須先決定愛的中心,因為善就是一種愛的實踐,那麼什麼是愛的中心呢?
藉由驚人的科學發展過程中,我們開始擁有相似於神的創造力,但卻還未能擁有相似於神的愛,為了擁有相似於神的愛,我們必須去實踐愛,並將生活導向善方。人應當把神,這愛的主體,作為善標準的中心。神是萬物的中心及本質,儘管祂的被造物,這個現實世界,是如此無常且多變,然而祂的愛仍是不變且永存的。 (第一屆 ICUS,1972.11.23-26,紐約)
我想,不只是我,許多人都已經開始察覺到科學所帶來的某些不良的影響,雖然長久以來科學在提昇人類福祉的貢獻上呈現了不止息及卓越的佳績,但我發現,今日的人們正一點一滴地喪失對科學的主管權,那就如同人們對自己所投入研究發展的科學之主管力正逐漸地喪失,假如這樣的情況仍舊不斷持續,我們將難以保證將來不會有失去控制的情形發生。
人們喪失對科學的主管性乃是在於科學發展的過程中,科學在本質上傾向於會主動地排除有關人性及道德觀問題的考量,隨著歲月的更迭,科學的分門別類越來越細,走向需大量的分析及數據化,完全忽略了道德與價值的問題。於是,人類對科學的主管權已逐漸衰微以致沒落。我確信,在所有會引發科學研究的動機中,最終及最重要的動機乃是為了人類的福祉、繁榮及和平,這想法並沒有錯。然而,越為細分的科學領域及越走分析論的研究方法,使得科學的發展已漸漸脫離原本的初衷。原是萬物環境主宰的人類,本來期待著的是人類普及的繁榮與幸福,但相反地,科學的成就長久以來所成就的,是在環境及新的生活型態(屬於對象立場)上的進步與發展,也就是說,當人們原本的期望能帶來人類(屬於主體立場)幸福,而科學所產生的成就卻是針對對象立場的環境帶來進步與發展。
人們的期望與科學的實際成就上的差異與不合,致使人類的主管權漸至衰微而消失,然而科學仍是有希望來解決人類最終極的主體性問題,如同它已經在對象性的環境及新生活型態上所作的努力一般。我深切的渴盼每一位科學家都能夠在各自所擅長的領域中,基於堅固的道德價值觀出發而後藉由採取心靈層面及整合性的方法,如同過去以著物質層面及分析性的方法一樣地來提昇人的尊嚴。
假使我們能推動科學以著人的尊嚴為中心,使之蔚為風氣,那麼有關污染這難以克服的問題,便能夠迎刃而解。而這兒又產生了人本然形象的問題,即是所謂人的本性。我的觀點是人的本然形象是以著善或價值為中心,心與體互相和諧授受,心靈與肉體能和諧地、合一地存在。我將科學的本然特性,視為如同人類一樣的有心與體兩面的結合體,這意即科學應該被視為一個統一體,也能處理有關道德價值觀的問題,或許我們可以把這綜合的科學稱作「文化科學」。然而,為了使科學可以處理有關道德價值觀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出現了,那便是這價值的標準從何而來?一般來說,價值觀的標準總是隨著時代及環境而改變,過去的價值觀標準與著現代的價值觀標準就有著極大的不同,而且東方國家又與西方國家有差異。因此,為了全人類普遍的利益與福祉所建立的真價值標準,必須是具有能適合於任何時間、空間之全球的與絕對的要素。絕對標準的建立意味著新道德價值觀的建立,這個絕對的標準應當是構成家庭倫理基礎的愛,因為在家庭中所存在的倫理關係之真愛是絕對的—永恆的愛—它將如同太陽光溫暖照亮萬物般地,讓每一個人的心中充滿喜悅與溫暖。無論是在東方或西方,這愛從未改變過。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可以思考到必定有一位絕對的存在,作為這絕對的愛的主體,我相信這位絕對的存在應是最有資格成為新價值觀的根本標準。
我認為這絕對的存在並非僅是概念上的存在,而是在人類歷史中,早已顯露出祂自己是一位實質的實體,我們知道,歷史上許多的聖賢哲人以及宗教領袖們都曾在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地區出現過,這些人呼籲並驅使著人們的良心去行善、去愛人,當人們回應並遵循教誨時,人民與國家都能享有和平與繁榮;但當人們頑強的反抗時,便會陷入混亂與衰敗之中,即使今日陷於混亂渾沌中的人們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等待著現代聖哲們來實現愛,所有的事實顯示出歷史的演進方向乃是為了實現愛的目的,因此我們知道,歷史的中心主軸乃是有意識地朝著一定的方向在進行著。我盼望能夠為大家來定義這實質的存在,這作為中心主軸立場的「絕對存在者」。我們可以看見的是,在所有人類歷史的現象面背後,這位「絕對存在者」計劃著經由聖人、正直的人們及有良心的領袖們來實踐愛,以建立起具有道德價值觀的世界。依據我的結論,假使這世界的人們能夠把這位「絕對存在者」視為人類歷史的中心主軸,那麼認知這道德價值觀的世界便不是難事了。 ﹙第二屆ICUS,1973.11.18-21,日本東京﹚